英国学者:中国崛起,应该如何应对美国的衰落(组图)
中国在崛起,而美国却陷入了相对衰落,这一现象在学术界引发了关于国际秩序中权力转移的一些讨论:这一过程是否能和平进行?这一过程在何种条件下进行?历史上有什么类似先例?那些先例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约瑟夫·帕伦特(Joseph M. Parent)和保罗·麦克唐纳(Paul K. McDonald)刚刚出版了一本很重要的书籍《巨人暮年——大国的衰落与收缩》(Twilight of the Titans: Great Power Decline and Retrenchment),两位作者在书中使用定量方法对权力转移过程进行了分析。他们针对崛起的中国发出了警告,而且还就衰落中的美国该如何恢复昔日地位给出了自己的路线图。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科丽·沙克2018年11月24日在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评论文章:《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美国的衰落》
哈佛大学政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把美中两国所面临的困境称为“修昔底德陷阱”(the Thucydides Trap),它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处于相对衰落中的国家面对崛起的挑战者十分恐惧,以至于这个衰落中的国家甚至为了阻止挑战者超越自己而挑起了战争。虽然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书曾受到一些批评,不过该书不但使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s)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且该书还发出了“美国与中国对抗将加速美国自身衰落”的警告,从这一点来看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的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
在撰写这部政治学著作的时候,为了提供足够多的例证,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例举了一些经不起仔细推敲的“体现大国权力转移”的历史事件,这也是他的这本书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例如,英国和法国在二战后曾向德国让渡了一些土地,这一过程是在美国充当这三个国家的共同担保人的前提下才发生的,美国的实力大大超过这些国家,而且美国对这一安排是非常支持甚至是有些催促的。其实,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和平的大国权力交接,那就是19世纪末英国与美国之间的权力交接。至于核武器是否有助于大国权力交接过程和平地进行,这还有待于事实来验证。
艾利森教授在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国际秩序中最强大的国家是否在行为方式上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呢?世界霸主(hegemon)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以及确保国际规则受到尊重的强制力的来源。一般来说,霸主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为所有国家都在为了建立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的国际规则而努力着。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英国“统治了海洋”,因此得以免受陆上规则的束缚;20世纪(尤其二战结束后)的美国成为了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或“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的缔造者。
约瑟夫·帕伦特和保罗·麦克唐纳研究了自1870年(在这一年人们开始进行可靠的GDP数据统计工作)以来所发生的权力交接过程,他们希望通过这项研究搞清楚国际秩序中最强大的国家以及排在其后的其他强国在行为方式上的特征。两位学者一共研究了16个发生相对衰落的例子,一些是霸权国家(hegemonic powers)发生相对衰落的例子,另一些是中等实力的国家(mid-level states)发生相对衰落的例子。
他们发现,大多数国家在面对自身的相对衰落时都做出了很明智的反应,他们都迅速进行了相应的收缩(undertaking prompt, proportionate retrenchment),因为他们希望在战略层面保持自己的“债务清偿能力”(solvency)——他们不想背负太多负担、不想破产、不想失去自己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曾使他们强大起来的明智策略在他们面对困境时也是有帮助的,而且那些明智的策略还促使他们缩小军队规模并避免与他国发生军事冲突。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收缩战略可以帮助他们保持原有的声望,而没有采取收缩战略的国家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他们还发现,处于衰落中的国家一般来说并不会被其它国家视为一个有诱惑力的攻击目标,一个崛起中的国家通常并不会去攻击一个正在衰落中的对手。根据二位作者的研究,其中的原因在于,处于衰落中的国家会尽力避免被卷入容易暴露自身国家实力的冲突或战争,衰落中的国家不会冒险去暴露自己正处于收缩状态。然而他们还发现,处于衰落中的国家一旦主动挑起冲突,那么它们在这类冲突中往往是获胜的一方。两位作者在结论中指出:“这说明处于衰落中的国家是灵活的、难以对付的(declining powers are flexible and formidable)”。
两位作者的联合研究显示:“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开启对霸权的争夺不仅将刺激外部敌对国家结为联盟,而且还将损害国内脆弱的长期增长基础”,在规划未来时往往将100年纳入视野的颇具智慧的中国战略家们本来是可以从这一结论中获益的。
不过,这对于国家实力正处于相对衰落轨道上的美国来说却是好消息。如果未来情况的发展与历史统计数据相符,那么美国很可能会在解决好国内问题的同时尽力避免被卷入战争,而中国则会激发起反对其继续崛起的“抗体”,如此一来形势将有利于美国恢复此前的国际地位。而在另一方面,这对于美国的盟友们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为了维护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秩序、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安全,那些国家将不得不承担更多开支、风险和责任。不过,这也正是我最为担心的一点,历史统计数据可能会使我们受到误导。因为在研究过程中,16个发生相对衰落的例子被两位学者赋予了同样的重要性。相较于他们的研究结果来说,有两个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可能会更加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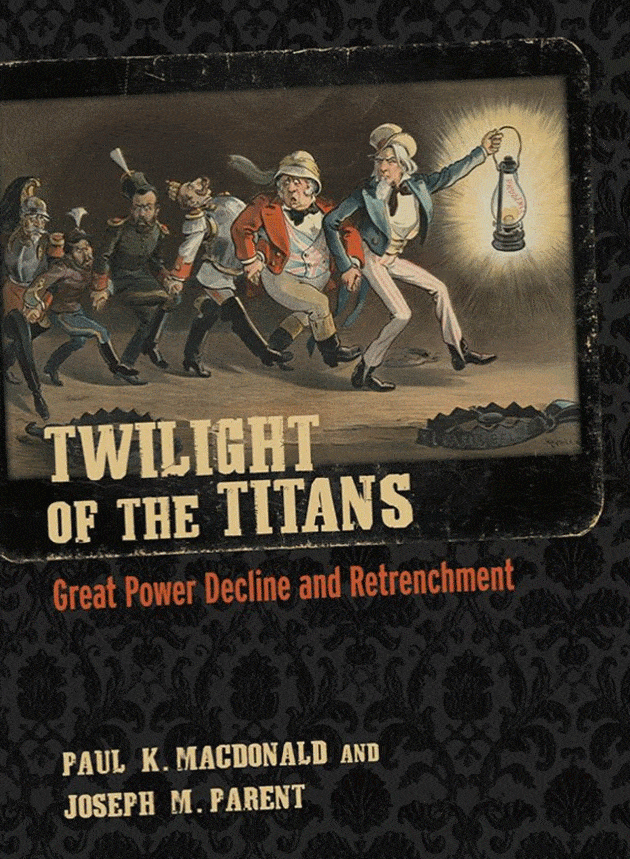
保罗·麦克唐纳与约瑟夫·帕伦特共同撰写的政治学著作《巨人暮年——大国的衰落与收缩》一书封面
首先,一个国家是从头把交椅上跌落还是从靠前的几把椅子上跌落,意义大不相同,前者比后者要痛苦得多。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强大而重要的国家,然而他们之间的排名差异并非都是那么引人注目。德国人会关心自己的国家是第三大还是第五大经济体吗?也许会有一些德国人关心这个问题,不过基本上人们不会太过在意。然而各国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坐上头把交椅还是非常在意的,因为这一地位将赋予他们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如果中国成为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么中国将改变美国时代的诸多规则:好恶将取代法制,小国将听命于大国。我们已经在中国与邻国的互动中、在其掠夺性的贸易和商业活动中看到了这样的迹象。美国及其自由主义盟友们将竭尽全力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第二,国家的性质比两位作者所认为的更加重要。他们发现在政权类型(也就是国家的性质,即共产主义、极权、民主等性质)与战争是否爆发之间并无关联。自1870年以来所发生的16个权力交接过程中,英国共衰落了6次(两位作者甚至文雅地将英国称为“在衰落方面最有经验的国家”),而德国则崛起了8次。也许真如两位作者所总结的那样,“对处于衰落中的国家发动进攻并不常见,那是很少发生的例外情况”。在他们的历史统计数据中,只有上升中的德国在面对衰落中的对手时变得极权而富有进攻性。英国经历了多次和平的相对衰落,可见英国非常善于在实力衰落时展现自己灵活的应对技巧。我们从英国和德国的案例中很难归纳出关于衰落大国行为的某种理论,我们从中看到的其实更可能是英德两国各具特色的战略文化。这两个国家可能都是特例,通过这样的两个特例来建立某种理论是不合适的。
政权类型的重要性也许被低估了,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韧性和恢复能力。两位作者发现,“一个衰落中的国家完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是不太可能的,不过要想有所恢复,那么收缩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意味着一个正处于相对衰落中的国家必须看清自己的状况并做出政策调整。在这个时候,极权国家往往比民主国家更加缺乏弹性,它们会在错误政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人们一直在讨论一个大国的衰落是否将在国际体系中引发战争,《巨人暮年——大国的衰落与收缩》一书为这场讨论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两位作者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并试图通过总结过往大国和中等实力国家发生衰落的例子来得出答案。这不仅是个有趣的学术问题,他们用令人信服的论据证明:对于衰落中的大国来说,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将事与愿违(fighting preventive wars is self-defeating for declining powers)。一个正在衰落中的大国应该收缩、做出妥协并避免被卷入冲突,而不是对崛起中的挑战者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如果美国能采纳两位作者在这本书中的政策建议,那么美国将逐渐学会如何与“有中国特色的民主”(dem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在这个世界上共存。有趣的是,这一政策建议也正是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他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所主张的。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