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亚洲的理解急剧减少,澳前政治高官:澳洲需要开放,别再当华盛顿“跟班”(组图)
本文译自Pearls&Irritations,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澳洲前总理和内阁部秘书长John Menadue在Pearls&Irritations网站发表了题为《我们的国家未能为亚洲做好准备》的评论文章。
全文如下:
在我为Albanese总理访华准备的简报中,我说过:
“澳洲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府制度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必须相互学习。否则,我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
作为一个定居者社会(settler society),我们紧紧抓住英国、欧洲和美国的历史不放。我们对自己生活的地理环境充满恐惧。我们至今未能调和我们的历史和地理。”
我们仍然不愿意拥抱我们的亚洲地区属性。
我们需要更加了解亚洲。不幸的是,我们的学校、大学、企业和媒体对亚洲的了解急剧减少。
我们从亚洲学习的撤退,已经成为一种溃败。 我们对亚洲,尤其是对中国的学习和了解,几乎在任何测试中都是不及格的。
为Anthony Albanese准备简报的人中,很少有人对亚洲有丰富的了解或经验。许多人都是Paul Keating所说的“澳洲裔美国人”。
随着澳中两国敌对关系的缓和,我们有机会促进文化理解和个人联系。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图片来源:网络)
11年前,我发表了以下演讲。当时我对我们对亚洲的了解持悲观态度。
从那时起,情况就明显恶化了,尤其是在我们的“白人媒体”上(White Man’s Media),由于无知和狭隘,对中国的攻击持续不断。
我们习惯于听命于华盛顿,也习惯于按华盛顿的意愿行事,以至于我们很难自己决定什么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随着一个新的参与者——影响力急剧增长的中国在我们地区的出现,我们无法独立思考的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作为美国的代理或矛头,我们在我们的地区没有长远的未来。
澳洲目前歇斯底里的反华言论并不令人意外。我们的媒体和商界对我们的地区严重无知。
正如Paul Keating所说,如果我们不对亚洲有更深入的了解,就无法在本地区内找到安全。我们对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了解过多并受到诱惑。对大多数澳洲人来说,亚洲是一本合上的书。
自从我们作为一个小型、偏远的“白人”英语社区在这里定居以来,我们一直害怕亚洲及其庞大的人口。
我们一直依附于遥远的全球大国来寻求保护——先是英国,现在是美国。一些人正在努力寻找摆脱对亚洲的恐惧的出路,但我们的恐惧不断抬头,很容易被机会主义者利用。
我们已经克服了“白澳政策”绝大部分的问题,但它却不断卷土重来,尤其是自John Howard和韩森(Pauline Hanson)时代以来。
Tony Abbott和莫里森(Scott Morrison)妖魔化寻求庇护者的运动,实际上是种族问题运动的掩饰。
(图片来源:路透社)
反对中国投资的运动,实际上是30年前敌视日本投资的翻版。
1980年代,我们的媒体充满了对日本投资的敌意:
“当地社区开始觉得日本人并没有公平公正地竞争。”(《澳洲金融评论报》1988年4月7日);
“天衣无缝的一块布——公司与政府交织在一起”(《悉尼晨锋报》1987年5月23日);
“日本最大的20家公司仅用一年的利润,就能买下整个新州”(《悉尼晨锋报》1987年5月23日),
尽管和最近的中国在澳洲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存量相比,日本的所占比例很小。
进入“休息期”
如果考虑到亚洲的存在——学生、游客和贸易,这似乎有违直觉。但与20年前相比,我们在亚洲问题上的准备程度可能有所下降。
在1980年代和90年代初,即Garnaut报告发布之时,我们在亚洲语言学习、媒体对亚洲的兴趣以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取得了进展,但在过去20年里,我们在这些方面却一直处于“休息期”。
亚洲语言学习和大学教育经费相对减少。
Hawke政府和澳洲政府理事会(COAG)制定的亚洲语言国家政策也已陷入困境。大多数亚洲语言学习陷入了危机。法语学习更受欢迎,这可能有助于游客在法国阅读菜单,但对我们地区的帮助不大。
澳洲媒体仍停留在与英美的历史关系中。
来自亚洲的新闻往往是怪异、滑稽和具有威胁性的。在亚洲陷入纷争的澳洲人是一个永远被纵容的例子,尤其是我们在巴厘岛的毒贩。
澳洲广播公司比其他媒体做得更好,但它仍然关注伦敦和纽约的琐事和遗留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对美国和英国读者来说可能很重要,但我们并不是一座停泊在伦敦和纽约附近的岛屿。
我们对欧洲的大部分报道也都来自英国,这当中伴随着英国人对欧洲惯有的偏见和谩骂。
Tony Abbott从总理和内阁网站上删除了关于澳洲和亚洲世纪(Australia and the Asian Century)的报告。在Albanese政府执政期间,访问该报告的权限一直没有恢复。
(图片来源:网络)
我们为什么进入“休息期”?
变革总是令人痛苦的,白澳政策的终结,尤其是Fraser时期的印度支那计划(Indo-Chinese program),以及Hawke政府随后的经济结构调整,都让许多人感到不安和痛苦。
Keating在变革方面也毫不逊色。他几乎连夜成为亚洲的忠实信徒。他开足马力,与印尼签订了防务条约,提议建立澳洲共和国,以表明我们的未来不再属于英国君主。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没有很好地应对这场变革。
不安的社会也为Howard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向我们保证,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可以再次感到“放松和舒适”。
对亚洲的恐惧源于对亚洲人数的暗示和随后的船只抵达。Howard是亚洲参与和亚洲扫盲进程中的一大障碍,尽管他在晚年担任总理期间曾试图改正自己的方式,特别是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
但是,失败的不仅仅是媒体。我们的商界也让我们失望。
(图片来源:网络)
商业理事会反复告诉我们,商业领域未能为亚洲市场提供必要的技能,这是开发澳洲在该地区的潜力和提高本国生产力的主要障碍。商界没有审视自身的表现,整顿自身的秩序。
我认为,在我们排名前200的公司中,没有一家公司的主席、董事或首席执行官能够流利地讲任何一种亚洲语言。
他们对提高自己或员工的技能兴趣不大。他们任命的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
企业对亚洲缺乏了解和认识,这意味着拥有亚洲相关技能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他们所希望的就业机会。在就业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人走进了死胡同。
1990年代,我认识并鼓励了许多掌握亚洲技能的澳洲年轻人。不幸的是,他们不得不去海外工作,例如到香港或日本为跨国公司工作。
这是多么大的损失!澳洲的雇主就是不明白这一点,而澳洲的纳税人却要为此买单。
Julie Bishop的New Colombo计划,也可能面临类似的问题,因为澳洲公司对雇用从亚洲学成归来的澳洲年轻人兴趣不大。
太多的澳洲企业投机取巧,将亚洲视为客户而非合作伙伴。
从长远来看,贸易和投资关系到信任和理解。这不是通过中介或翻译就能实现的。我们的大公司对亚洲的兴趣正处于低潮。
对澳洲企业进行的一项又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在澳洲经营的澳洲企业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亚洲和/或亚洲技能或语言的了解甚少。一些澳洲企业高管最接近亚洲的机会,就是在香港观看七人橄榄球赛。
现在,有数以万计在澳洲出生的亚裔公民就读于我们的大学。
这些在澳出生的年轻人,更有可能因为优秀的成绩和职业道德被录用,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技能。他们可能会像1990年代那样逐渐流失。
对于企业主席、董事和首席执行官来说,现在学习亚洲语言技能显然为时已晚,但他们是否正在为未来招聘具备必要亚洲市场技能的高级管理人员,这一点并不明确。
想要打入舒适的董事俱乐部是非常困难的。这个俱乐部需要彻底改革。
也许我们不需要一门亚洲语言,也不需要太多的商业技巧来挖掘铁矿石和煤炭并将其出售给非常愿意购买的买家。
但在出售葡萄酒、精心改造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尤其是旅游业,我们肯定需要这样做。

(图片来源:网络)
亚洲旅游业蓬勃发展,但我们的回头客不够多。
我们从一个新市场跳到另一个新市场-——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现在是中国。澳洲旅游委员会在鳄鱼先生Crocodile Dundee和奥普拉(Oprah Winfrey)等营销大戏上花费了大量资金,而它本应着眼于改进产品。
很多时候,非英语旅游团在澳洲的旅游往往像在茧中一样,他们在由自己的同胞管理的范围内活动,与澳洲人隔绝,而澳洲人本应受雇为他们提供服务,帮助他们体验愉快的澳洲之旅。
在亚洲取得成功需要长期的承诺,但薪酬待遇和股东的要求却与短期挂钩。澳洲的企业治理未能让我们做好迎接亚洲世纪的准备。
澳洲的商界人士仍然是“男性化、呆板和苍白”,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兴趣与他们招聘的人一样有限。
中国和美国——与野兔奔跑,与猎狗狩猎
正如Malcolm Fraser在2012年Whitlam演讲(Whitlam Oration)中简明扼要地指出的那样,“无条件地支持(美国),会削弱我们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
一方面告诉中国人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另一方面却阻止他们的投资并接受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的驻扎,以遏制他们的影响力,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像这样“和野兔一起奔跑,和猎狗一起狩猎”,这与发展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完全相反,甚至有些奇怪。这种做法终将对我们产生影响。

澳洲总理Anthony Albanese和外交部长黄英贤。(图片来源:网络)
外交措施
外交在于说服,而说服他人并取得合作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提出一个既能满足对方自身利益,又不会严重损害我方利益的想法。
举例来说,在澳洲,很少有人知道印尼的利益是什么。我们上一次听到一位部长、政治家或商界领袖这样谈论印尼是什么时候?
印尼正在取得长足的进步。我们对印尼的描述却总是与牛、巴厘岛上的澳洲毒贩和避难船有关。
人们的兴趣被定期激发,但却很少有后续行动。
公共部门
澳洲公共服务部门,尤其是外交贸易部(包括澳洲贸易投资委员会,Austrade),比商界做得要好得多,但还远远不够。
我们的外交技能正在严重衰退,外交和贸易部被边缘化,以支持国防和“情报”(五眼联盟)的利益。
结论
Donald Horne在1960年代曾说过:“澳洲是一个幸运的国家,由那些分享其运气的二流人物管理着”。这句话现在依然适用,尤其是对今天的商界和媒体来说。
关键是澳洲要开放......向新人、新投资、新贸易、新语言和新思想开放,并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不要再唯华盛顿马首是瞻。
盎格鲁-凯尔特文化(Anglo-Celtic)既丰富了我们,也困住了我们。
*本文作者John Menadue是Pearls and Irritations的创始人和主编。他曾在Gough Whitlam和Malcolm Fraser执政时期,担任总理和内阁部秘书长、驻日本大使、移民部秘书长和澳洲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Rayyan)
本文译自Pearls&Irritations,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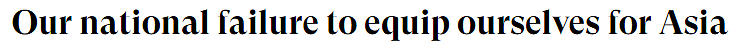







 +61
+61 +86
+86 +886
+886 +852
+852 +853
+853 +64
+64


